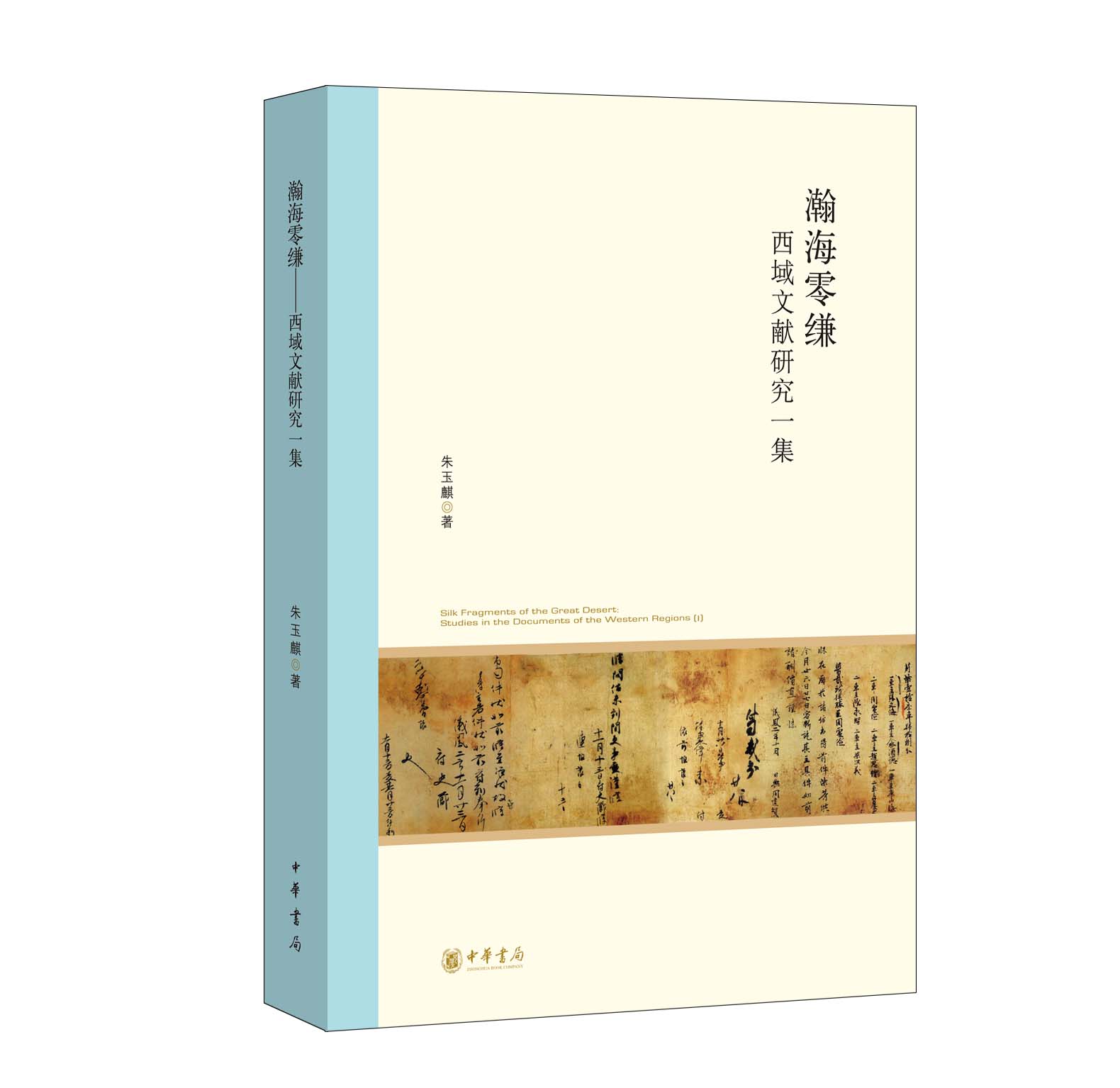
序 言
1. 汉唐西域纪功碑考述
2. 汉和堂藏《裴岑碑》旧拓考
3. 龟兹刘平国刻石的发现与近代新疆
4. 内藤湖南未刊稿《龟兹左将军刘平国碑考证》研究
5. 所谓“李崇之印”考辨
6. 吐鲁番文书中的汉文文学资料叙录
7. 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汉文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以吐鲁番文书为中心
8. 新出吐鲁番文书中的古诗习字残片研究
9. 吐鲁番文书中的玄宗诗
10. 新出吐鲁番文书《论语》古注与《孝经义》写本研究
11. “北馆文书”流传及早期研究史
12. 吐鲁番元代纸币的发现与早期研究
13. 伊犁将军松筠研究二题
14. 思想与思想史的资源——魏源致徐松三札考论
15. 良朋相与志春秋——《蒙古游牧记》成书考
16. 《行程日记》作者及相关人事考
17. 《疏附乡土志》辑佚
18. 《新疆图志》综论
19. 清代新疆民族教育的政府反思与对策——以《新疆图志·学校志》为中心
20. 王树枬与敦煌文献的收藏和研究
21. 王树枬的西域胡语文书题跋
22. 王树枬与西域文书的收藏和研究
23. 王树枬吐鲁番文书题跋笺释
24. 段永恩生平考略
25. 段永恩与吐鲁番文献的收藏和研究
26. 奥登堡在中国西北的游历——以汉文档案为中心
后 记
序 言
王炳华
玉麒兄大作《瀚海零缣》即将付梓,嘱为序。明知玉麒之研究,与我的新疆考古相去颇远;但关注点总涉新疆,个性虽有差异,文化内核总是相通的。故不惧无自知之明,还是乐意做这件事。
作为祖国的西部边疆,因自然地理环境,新疆富涵别具个性的历史文化遗产。它地处亚欧大陆板块腹地,在十分久长的时段内,曾有太多肤色不同、语言各异、经济生活有别、人数多少不等的民族,在这里驻足,或以之为陆桥,东走西行。他们相遇、接触、交流,不可避免存在的不同利益追求,自然又会引发矛盾甚至冲突。但最后,又总会在融合之中前行,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一。第二,东亚大地的华夏文明,其影响很早就已进抵新疆,远及南西伯利亚、中亚、西亚和南亚,虽未见于汉文文献记录,但考古遗存确已揭明过这一事实。性质类同,方向相反,西部欧亚世界古代文明走向东亚,同样可以在新疆大地的古代遗存中见到消息。托新疆大地极度干燥之福,在新疆、尤其是南部瀚海绿洲,保留了这一类它处难求的历史文化鳞爪。这类历史文化中十分残碎、难成规模、不成系统的文物,极为珍贵。千差万别的社会历史,在其流逝的过程中,进入并得以保存地下的物质资料,只会是极少;在诸多偶然机缘下,遇到了考古学家的手铲、现身在世人面前,更是少数中之少数。这少之又少的鳞爪,获得准确识别,呈现特定的历史文化枝叶,需要热爱这片土地、相关历史文化的研究者艰苦的工作,才有可能完成一系列蜕变、演化,腐朽方可成神奇。
因此,研究新疆,准确认识新疆的历史文化,是一个十分宏大的文化工程。它要求研究者具有广阔的视野,有超过常人的多种语言、文字知识;要求研究者有多种相关学科的文化素养……尤其,最重要的一点,研究者得有对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他们的历史文化深层的爱的感情,这才可以在遇到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时,仍能坚持前行。玉麒在新疆生活、工作的时日不算太长,但对新疆这片土地,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对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有十分深厚的感情。他在研究工作中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之外,在诸多具体研究背后满溢着温暖的人文主义情怀,更让人难忘。这应该是研究新疆人、事、历史文化很重要的一种素养。
说玉麒热爱新疆这方水土,绝不是随便的溢美之词。这方面留给我的印象不少,只说近年相当深刻、关于黄文弼先生的一件事。在我几十年新疆考古的生涯中,曾听到不在少数的对黄文弼先生新疆考古事业十分偏颇的评论,都是忘却黄先生当年工作的具体环境,忘却他只身孤影在沙海、戈壁中苦苦前行,与“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华民族西来说”等为殖民主义张目的谬论相抗争,为维护国家主权、利益而奋力拼搏的时代背景。玉麒自然也是注意到这些现象、挺身而出为其正名的一员。
上世纪20年代后期,在中国大地上展开过的“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是与黄文弼、与中国学术界、也与新疆发生过密切关联的一件事。它的出现、展开、完成,有许多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地方。比如,认识中国的西部山川、地理、水文、气象,甚至历史、考古,当年以斯文·赫定为核心的瑞典、德国学者,竟有超过中国学界的关注度。仅仅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现象。当年的中国,积贫积弱;面对西方列强之侵凌,危难重重。在风雨如晦的时代,如何应对这一涉及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经济文化权益的大事,当年的政府真是软弱无力的。真正有力应对了这一挑战的,是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有国际眼光、有社会责任心,也有危机感;他们不惧挑战,敢于坚持国家、民族权益,也能睿智地因势而动、机智应对,既选拔优秀青年、藉机培养国家需要的科技人才,也因势完成我们自己本该做、过去未能做、现在可以争取做一点的利国利民的事情!真可谓是“铁肩担道义”!对近百年前曾经在中国西北、更多与新疆关联的这件事,是一件不该、不能淡忘,而应该认真、深入思考的大事,是一篇应该写、也可以大写的好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家慢慢淡忘的时候,玉麒在行脚瀚海、沉思往昔时,他想到了!今天已经耸立在乌鲁木齐新疆师范大学校园内的“黄文弼中心”、“黄文弼图书馆”,以及由黄氏切入、在2013年于新疆师范大学成功召开了的“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与此相关、很好完成了的、书写在新疆大地上的一篇好文章。这篇文章,引发过新疆、中国、甚至国际相关学人的关注,取得了很好的思想、文化教益。这些教益,仍然在、并且将继续发挥其影响。完成这篇文章,是新时代下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但这篇文章的发轫、展开、完成,诸多环节,确实是与玉麒密切关联的。没有他最初的思考,认真的组织、布局,一点点细致铺展,这篇文章是难以完成的。其背后的动力,是对新疆的关心、爱心,对认识新疆历史文化不变的初心。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瀚海零缣》,是作者在近二十年里戈壁、瀚海行脚时,认真思考过、完成了的部分文字的结集。看似无序,但实际也有内在关联。它们都是新疆历史进程中曾经存在、应该关注的一些历史的细节;一些问题,还是近年新疆历史、考古、思想文化界正在关注、讨论的问题。稍不同的,是《零缣》再次提及、剖析,有了更开阔的视野,吸纳了新出土的有关资料,展开了更严谨的分析。如《周书·异域·高昌传》中提到的“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子弟,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说,是学习、研究高昌历史的学人都会注意到、且人人都读过不止一次的,而《零缣》就觅得了“不必皆为胡语”的新意。阅读吐鲁番出土古文献,对唐代西州学童以稚拙笔法完成、而又有幸留存至今的许多习字纸,是见的不少的。部分断纸残页上仅存的聊聊不足十字,却被他追寻到了李隆基《初入秦川路逢寒食》诗作的消息;又从抄纸不同、字虽稚拙却又“力求工整”,捕捉到了作为李唐王朝最高统治者在边裔新疆也同样被顶礼膜拜,感受到了唐代文化、政治价值观在边远西州同样被深深接受的文化图景。这自然要求作者丰富的学科专业素养,更需要十分认真、细致深究的态度,不然,其真相是很难被捕捉并清楚揭示的。
这方面,最值得我们关注、思考的一点,是《零缣》中对“李崇之印”的考辨。它涉及的其实不只是对一方印文的考释,更是对一种浮躁学风的批评。将“李忠之印信”释为“李崇之印信”,并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相当数量涉及新疆历史的专著、专文中引用,是可以也应该进一步思考的现象。近百年前采集的一方汉印,印文确已比较漫漶,小篆中“崇”、“忠”字形也相近,这些都可以成为将“忠”误读为“崇”的理由。但真正导致大量重要著述、不少文章未加深究而径作“李崇之印”使用,最重要一点,还是在于“李崇”毕竟是西汉最后一任“西域都护”,史籍有文,通过“李崇”,可以在西域历史、两汉统治西域的故实中引发更多联想,于是就因循旧说,不认真细究印文这一浮躁学风存在关联的。这自然是必须予以挞伐、批判的风气。此风不清,会难以走近更真实的历史,背离了研究的初衷。笔者在主编《新疆历史文物》时,也有过这一错失。玉麒不为这一失误讳言,细想,更为他的认真感动。一种健康的学风,会助益研究的进步。这种既严肃、又平实的分析,为历史文化研究注入新风,不仅在新疆历史研究界、而且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都是很需要的。
《零缣》中的文字,朴素、平实,但深一层认识、细想,却能感受到平实、朴素文字背后饱含炽热的激情。书中涉及乾嘉以来不少与边疆相关的人士,如纪昀、松筠、徐松、魏源到王树枬等等,都是有思想、有影响、有种种故事的人。他们对汉碑、唐刻的访求,背后是对开拓边疆历史的关心,有着唤起人们关注边疆危殆命运的忧愁。这里,我只想着重说说李晋年,一位人们并不怎么熟悉的旧文人、小官员。他出生在清末,光绪二十八年(1902)举人,民国时期,新疆政治舞台上,还可以见到他的身影,在镇西(巴里坤)、巴楚、沙雅、墨玉等地主持过县政,参与编纂过《新疆图志》。玉麒有心,在日本访学,细察汉和堂主人陆宗润收藏之《裴岑碑》旧拓题跋中,发现了李晋年。继后,又在《北凉写经残卷》、《刘平国碑》拓片、《镇西厅乡土志》中觅得李晋年的消息,也是一位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西域大地的文人。所任官职不算高,但真办过不少实在事,如任职巴里坤时,利用龙王庙办过“官立第二简易识字学塾”,利用民房办过“官立第三简易识字学塾”;办学堂,提升民众的文化素养,这不大的好事,社会没有忘记。“辛亥革命前后,巴里坤民变,群推已经卸任的李晋年担任同知安抚大局”。民变——激烈的社会矛盾、冲突——使得现任官员已无法控制局面,要请已离任的李晋年出面收拾大局,这自然表明李晋年在当时巴里坤的口碑,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还是不错的。引了这么多大家可以在《零缣》中见到的资料,是想说明:玉麒在这里,已从碑石资料的追求中,走进了李晋年的生活、历史,倾注了他深深的感情。
而且不止于此,他还在继后的文字中,轻轻一笔,看似不经意地点出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已故西域研究专家李征(1927-1989)即其哲嗣”,让我这个在新疆考古所工作过40年、与李征有相当过从的考古人,无法不深感其别有一番情意在心头了!在阶级斗争风高浪急的岁月里,先贤李晋年自然不能是好人,留给李征的遗产,自然也是不会美妙的。带着“原罪”之身的李征,虽有家传的对新疆文物、历史的挚爱,但工作、生活是难求正常、顺利的。这是另外一件可以一说的故实。平日过从中,玉麒曾不止一次提及李征,问其生前身后事,虽可感他对李征作为我的同道、友人的关心,但应该说,直到这次拜读过《汉和堂藏〈裴岑碑〉旧拓考》后,才恍然大悟:在玉麒的这类文字背后,在他关于新疆历史、文化研究的背后,他是赋予和注入了自己的生命、感情追求的,从中可以感受到他血脉的搏动。所以,《瀚海零缣》虽然是作者从诸多细节中努力寻求的历史真实,但也处处感受到他对现实生活的浓烈感情和十分的关心。新疆历史文化的研究,对他来说,是生命的意义,是人生价值的追求。这自然是真正可贵、可以做好任何事情的最根本、最有力量的前提。
认识新疆,是一件大工程。要做好、完成这件大工程,玉麒兄对这片土地的思考、著述,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好的启示!
2019.3.4凌晨,草于
沪上朱家角镇玲珑坊小居
后 记
2000年以来,围绕着“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的研究,我一直在西域文史这一漫无边际的沙海里随波逐流。在这个新的领域里,在清史、西域史的多个方面,我都在补课。十几年来,我的研究体会是:任何一个细小的人文课题都不是封闭的、不具备扩展性的空间,研究的触角随时会引导你进入另外的天地。《瀚海零缣》正是围绕着原来的题目而上下求索、左右寻源的补课过程中,逸出于本题之外的一些零散文字的第一次结集。
通过文献梳理历史,是我对“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自以为是的正解,所以我的补课主要是处理过去没有接触过的与西域相关的文献;每一次新文献的邂逅,都是个人用以消除知识盲点、以求对于漫长的西域史建立起基本认知的过程。
对于西域文献特性的理解,我曾在近年开设的“西域文献研究专题”课程上,概括为“载体的丰富性、文字的多样性、时间的悠久性、表现的世界性”四个方面。这些特征,既是西域文献研究的魅力所在,也是从事研究的困难所在。此外,在强调文献是历史的碎片的当代史学观念中,西域史的研究尤其呈现为材料本身也是碎片的状态,如漫漶的西陲石刻、剪成了鞋样的吐鲁番文书、突兀而来的一件档案,等等。西域文史的研究因此而具有着双重的碎片特质。我的点滴摸索,更是呈现出一鳞半爪的状态。
虽然只是一些零碎的成果,在这些文章结集的时候,我仍然要感谢在这个领域的探索里给予我支持的师友,每一个问题得以解决,从文献阅读到思路启发,都得益于他们的帮助。这种援手,有时出现在我的一个小小的注解里,有时甚至没有标注。
特别要感谢荣新江老师,是他的指引,让我从清代新疆的典籍文献上溯,对中古时期的写本文书和更早期的石刻史料有所涉猎。毫无疑问,在文献学的领域里,处理这些不同时代、不同载体的文献,如果没有专门的机缘和指导,断难轻车熟路。
感谢西域考古的前辈王炳华先生,他的西域研究在考古文物与历史文献的结合上,始终是我学习的榜样;值此论文结集,得到他欣然赐序,更是对我继续努力的鞭策。
我还要感谢最初发表这些文章的刊物,使得拙稿得以在结集之前获取了接受批评、指正和完善的机会。此次结集,除了统一体例之外,也对文章做了不同程度的补正工作,因此,读者引用,还请以此结集为准。
我更要感谢冯其庸先生,自1990年代以来,是他带我完成了走遍天山南北的考察征程。很多年前,在通州且住草堂,又是他,为了鼓励我的研究,为我打算完成的系列论文题写了“西域文献研究论集”的总标题。如今斯人已逝,而精神犹在。
这本书纪念冯其庸先生——我在西域行旅中永远的导师。
朱玉麒
2018/12/24于北大朗润园